古代斩首,为啥一定要推出午门?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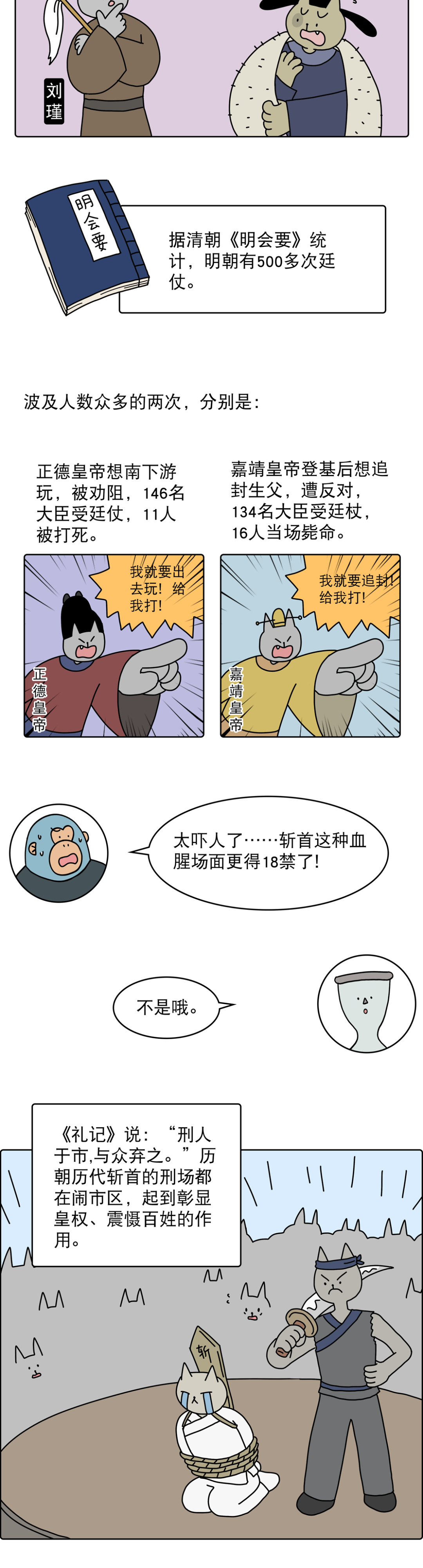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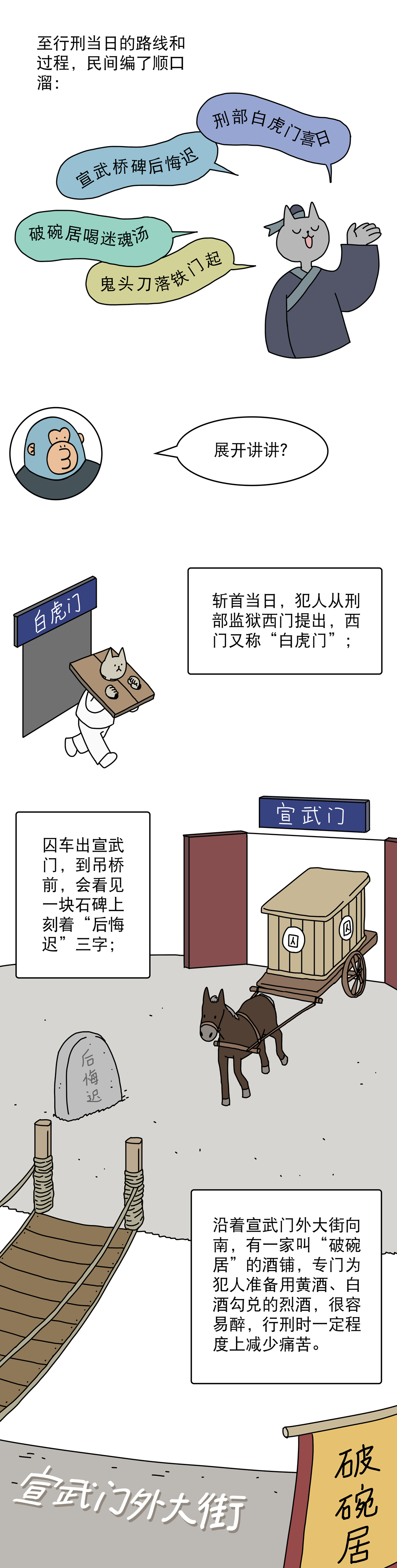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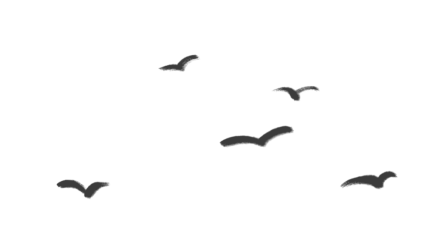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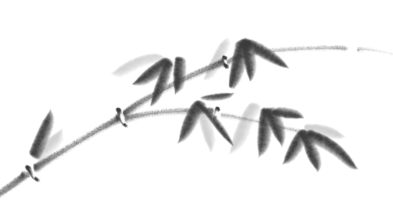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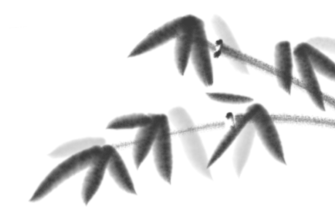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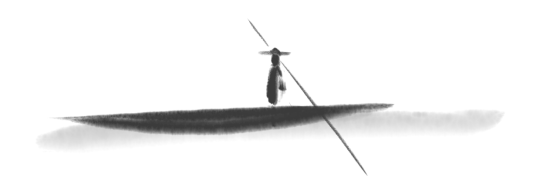
大宋寻真客
第十一章 糖墩儿
1
清爽柔和的夜色从远处似有还无的山峦处慢慢地浸染过来,照着薄薄的白色床单在风里飘荡。
一个影子出现在布单后面,小小的,一闪而过。
南来猛地撩起布单,什么都没有。
身后响起一声轻微的脚步,他又迅速回头,依然只有床单在飘荡,只是,地上的砂石印出半个脚印。
陈寿说他和陈露水一起去地里了,这院子里的人……南来能感受到,那人正凝神聚气。
于是他闭上眼睛,也运起气来。在陈家修养的这一个月,他的内力不仅没有受损,反而像是有所增益,这一运气,更觉心底澄明,五感通畅。
西南方向有一缕逆流,正向着自己侧前方冲去。
他腿脚不便,没有直接攻向西南方向,而是快速向侧前方飘荡的床单出了一掌。床单柔软单薄,像一张网,将他的一掌力道缓冲后散向四周。
一身闷响,床单后果真有一人被推开,像是半跪着向后滑了一尺距离。南来顾不上腿伤,也顾不上刚刚洗好的床单,飞身一扑,拢着床单将要逃跑的那人裹了起来,然后借势系了几个结,把那人牢牢固定在床单里。
此人藏匿的干净利落,轻功绝对在自己之上,应该不是普通的毛贼。这么想着,南来猛地将那人头上的床单扯开,大喊道:“居然敢来这里偷鸡摸狗!”
“啪!”
一巴掌狠狠扇到了南来脸上。
那露出来的面容是愠怒的陈露水。
南来愣住,脑子被打得嗡嗡作响。仍被裹在布单下的陈露水整张脸憋得通红,头发散乱地糊在脸上。见南来还在发呆,她下肢用力,一脚把南来踢飞了出去。
暮色四合,墨蓝色的夜空像纱缎一样铺展着,星斗闪烁,鼻青脸肿的南来和陈露水坐在门口仰头看着天空,两人都看得出了神。
直到陈寿扛着锄头,回到院子里,惊道:“你们怎么了?”
“有贼。”
两人异口同声,说完看了看彼此,似乎有些尴尬。陈露水赶紧补充了一句:“已经赶走了。”
陈寿做了一天农活,已累得没什么力气了。他点了点头,撂下锄头就进房里休息了。
又是一阵寂静。
陈露水先开了口:“床单,得重新洗吧?”
“我来洗,是我的错……”
“你可曾习过什么心法?刚刚是怎么发现我的?”也许是入夜的缘故,她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。
南来摇摇头:“我只会些外家功夫,未曾练过心法。你轻功好,我能发现完全是多留了些心。”
“那你还挺有天赋的,”陈露水笑,看向他,“不如我教你轻功,你教我刀法?你那把穿云刀确实挺不错。”
南来怔了怔:“我自然是愿意的,但这会花费不少时间。”
按他的恢复速度,最多再有半个月,他就能正常跑跳了。
“你还是要去保州?”
“是的。”
“不能先留下来学功夫?”
“没有时间了,老爷和瀛州百姓都在等着我。”他口中确定,内心却有些摇摆。
啪,后脑勺挨了一掌。陈露水不知为什么又恼了起来,说:“等着你……你真以为自己能救国救民吗?”
“最起码找人这件事,我还有可能做到。”南来嘟囔。
“只因为你没有妻儿老小,所以才如此狂妄,如此不管不顾地逞英雄!到时候小命没了,也没有人会觉得你伟大!”
南来被陈露水一番呵斥,气势上已弱了下去。而且陈露水这话,他总觉得似曾相识。
没错,当初在小井村的时候,那老者在十年前也对江山澍说过同样的话。
南来缩了缩身子,紧了紧衣襟:“我想做到,只是因为答应了老爷。”
陈露水看向南来的眼睛,那眼睛像是一汪见底的清水。
他说:“我只是个普通人,除了信守诺言,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我对自己没有一定要成大事的期待,对你也没有。”
“对我没有期待,是想说我也做不成大事,是个废物?”
南来先是摇了摇头,但又觉得不对,随后竟然又点了点头。
陈露水见状,伸手要打他,他赶紧又摇摇头,急急地护住脸说:“没有期待不代表就是废物,你虽不能算英雄,但我也是喜欢的。”
话音刚落,南来和陈露水的脸就都红了起来。
南来慌了神,解释道:“我是说,你有一身武艺,还懂医术和占卜,很让我敬佩,但我不想你投军或者离开陈叔。”
身后的木屋门缝里流出一缕金色的烛光,似乎还有陈寿隐约的鼾声。
“我只盼着你和陈叔能平平安安,吃饱穿暖,做平常的事,过平常的生活。”
不知为何,他的脸还是一片绯红。此刻夜风骤起,星斗竟也微微摇曳,如一池涟漪。
接下来的日子,南来除了做院子里的活计,也会跟着陈寿和陈露水一起进田。走在田埂上,他能看到远处焦黑的地平线。那是大井村的方向。那里仿佛人间地狱,他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,只是每每想到那片惨象,依然心有恐惧。
田野上吹来湿润的风,带着一丝芫荽的气味。五月正是播种芫荽的好季节,陈寿说,陈露水向来不喜欢芫荽,极讨厌这味道,但他们只有芫荽菜种,也不得不将就。甚至现在田里的这些芫荽,也多是陈露水亲手种下的。
南来在窄窄的田埂上小跑了两步,紧跟上走在前面的陈露水,笑道:“你喜欢吃什么?”
这问题来得没头没尾,陈露水怔住:“什么?”
“你既然不喜欢芫荽,总该有些喜欢的吃食吧?糖墩儿?熬稃?”
南来在她身边晃来晃去,陈露水猛地将左肩扛着的锄头换到右肩,似是借机要驱赶他,“说这些做什么?现在又吃不到。”
“说说又不妨事,等我将此地灾情托老爷上禀,再找到江山澍,击退辽人,修好去保州的大路,想吃什么都有。”南来轻轻说着,迎着微风眯起了眼睛,带着淡淡笑意。
陈露水的脸颊红了些,她低着头,似是有些烦躁地嘟囔:“你倒想得远,真是会做白日梦……”
“你说啥?”南来凑近了些。
“糖墩儿。”
2
“保州第一公子”唐公子最近总是在生闷气。
或许是天气渐热让他心浮气躁,或许是因为他总是想到那个这几天都没再见到的人:夏竦。
总之烦得他又多掉了不少头发。
自从秘府建成后,夏竦就没再出现了,不知那秘府里面到底在做些什么。这保州还是不是他的地盘了,居然有他不能插手的地方。
这天他装作遛弯的样子走到门口,居然被佩刀侍卫拦了下来。
“我爹是录事参军,也不能进?”
“不能。”
“我是夏竦的好朋友,也不能进?”
“不能。”
唐福尔吃了闭门羹,更加抑郁了。夏竦和他爹或许真的是什么大人物,今后不要因他过去的行为找他麻烦才好。
这么想着,唐福尔溜达着去了清漪茶馆,平日里,富家公子都会来此喝茶清谈。店里人不多,他的好友开国男邹封之子邹忱也正好在。旁边还有一桌坐着一个紫衫男子,看着像是路过歇脚的,正在低头饮茶。只不过别人的茶汤都是绿的,他杯子里却是清的,还有股醇香。
唐福尔没在意,开口便向邹忱道:“邹兄,我或许是遇到大麻烦了。”
接着便将自己对夏竦的那点想法尽数说了出来。邹忱不以为然:“唐兄有点庸人自扰了。”
“我可是往他碗里啐过唾沫的,谁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来?”唐福尔还是很愁。
“我说唐兄莫要庸人自扰,其实是说这事还是有法子可以解决的。”邹忱一副运筹帷幄的表情。
“邹兄,快讲讲!”
“办法一,静观其变,他若真的要报复,你就抓好证据,完事后去州衙里狠狠告他。”
“这不妥,他若是找人打我,我还能真挨了这顿打不成?”
“那便是方法二,先下手为强,给他一个下马威,让他知道在保州就得忌惮你唐福尔三分。”
“如何给他下马威?”唐福尔来了兴致。
“像你说的,找人打他一顿啊。”
“可他府上都是禁军,我去哪里找比禁军士兵还厉害的人?”
邹忱笑笑:“唐兄有所不知了吧,江湖之大,高手那是一抓一大把。我听闻真定府有一春峰阁,其阁主刘铁树就是一个绝世高手,但他不像其他武林人士那样有各种穷酸讲究,拿钱办事,特别爽快。”
“这可太好了,邹兄能请来这位刘阁主吗?”唐福尔眼神发光。
邹忱笑得更加肆意,嘴上却不说话,只是两只一捏。唐福尔立刻明白了,“放心,银子管够!”
“莫道……谗言如浪深……”
唐福尔和邹忱前脚话音刚落,耳边就传来了一句歌声。歌声虽悠扬,却略显萧索,与之相伴的,还有零落的三两琴声。
两人转头一看,只见旁桌那紫衫男子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把古琴,缓缓弹奏了起来。
“莫言迁客似沙沉……千淘万漉虽辛苦……吹尽狂沙始到金……”
两人并没有在意唱词中意,只当是个酸文人,嗤笑两声,结伴离开了。
待他们走出茶肆大门,紫衫男子的歌声也停了下来。他将自己的酒葫芦掏出来,往杯里倒满了酒,一饮而尽。
“我不欺人,却有人欺我……”他笑着叹道。
他听明白了唐邹二人刚才的全部对话,虽不清楚他们要对付的人具体是谁,但他很确定那姓唐的小肚鸡肠,蓄意挑事在先,听信姓邹的谗言后,还要继续加害对方。
他从不对没有武功的人出手,但若坐视不理,妄为一代侠士,且不是和“那个人”成了一样的人?更何况还涉及老熟人刘铁树。
他是从真定府搭了商队的马车来的保州,料想那少年还得过几日才能到保州,既然暂时无事可做……
他一定要去凑这个热闹了。
